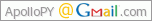不知道听谁说过,没有伤痕的女孩是不会爱上吸烟的。
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,是不会爱上伤口的;
我想一个没有受过伤害的女人也是不会爱上烟的。
烟是对那些美好细节的缅怀。做着一个神情忧郁的女子,坐在冬天忧郁的场景里吸烟的姿势,总是让她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。
我猜想此时此刻,她内心的疼痛,正象蓝玫瑰一样绽放。
烟是短暂的,所有销魂的东西,都是短暂的,而美丽也因为短暂而更加美丽。受一点点伤,就会哭泣,那是单纯的少女,但是吸烟的女人却不会轻易哭泣,选择烟,也就选择了一种绝美。
爱是一种伤害,但女人们却在伤害中寻找快乐。烟也是一种伤害,但同时,烟又让女人忘记了伤害。如果说,不吸烟的女人是一抹胭脂红,那么吸的女人就是一朵曼陀罗。烟渐渐飘散,飘不散的是风情和幻想。
一支烟。对于女人来说,究竟意味着什么?或许是情欲的颠峰,或许是分手的凄恻。没有伤害的爱是不完整的。
想起或者忘记那些爱过的和伤过的人,都需要烟。
烟不是一种生理需要,烟是一种心理需要。
长长的,细细的,烟在清滢动人的纤指之间燃烧。
如同那深蓝色的指甲,有一点深邃,有一点慵懒,有一点妩媚,有一点温婉,还有一点迷情。
一支烟,更象是一种别离。
坐在暗橙色的咖啡馆里,散发着恬淡的芬芳,所有的阳光都围绕在身旁。
窗外,所有的人都行履匆匆,每个人似乎都知道自己的方向。
吸烟的女人,内心冰凉如面一朵凌霄花。
一本发黄的书,一杯黑咖啡,一句让人心跳的诗,带回了那羞涩的少女时代,那时,什么都不懂,生活里只有浅绿色的梦。
足音清脆,让所有的目光都停止呼吸。
背影,如同一朵迷情的云,让多少风停止歌唱。
说话的声音,轻轻的,甜甜的,多象一阵春雨,那么忧伤,那么洁净。
那时候,为书中的故事,流下了多少可爱的泪水。
可现在,在也不会了,因为她自己也成了故事里的人物。
每个女人的命运,都是悲剧。因为,对于女人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短暂。
年轻的时候,想象在一个人的手心里渐渐老去,那种感觉是很温馨的。
因为,那时并不理解什么是老,以为那是一种至深的浪漫。
现在,当岁月无情地在脸上刻下伤痕的时候,才发现苍老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魔鬼。
老了,就是烟即将燃完的那一瞬间。
揿灭了烟蒂,又点上一支,但是发现了她的眼角,那一抹潮湿的晶莹。
烟在静静燃烧。上午的咖啡馆,如同一个没有睡醒的少妇,低低回旋着清淡的音乐。
与其说坐在椅子里,还不如说是陷在椅子里。
那一张原木的椅子,如同一只花篮,只是里里面躺着一支灰色的玫瑰。
整个上午,都沉浸在这样一种朱古力的温情里,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
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,人渐渐多起来,缓缓地挪了挪身子,她想要站起来,一看,烟盒里还有最后一根烟,又坐下,点上,火柴划亮了暗淡的角落,脸上显露出那忧郁深深的痕迹。
人们的说话声,使她感到不安。没有将烟抽完,就起身离去,脚步很轻,姿势轻的象一只猫一样。
然后,消失在十二月冰冷的风里,没有痕迹……
长长的、细细的烟,有时候是为了情绪的宣泄,胜过为了感受烟过喉咙的悲怆。虽然我很不耐烦那种为女人道具的凉烟。有的人点燃一支烟,不是为了多一些“成熟”的风情,只是为了怀念……